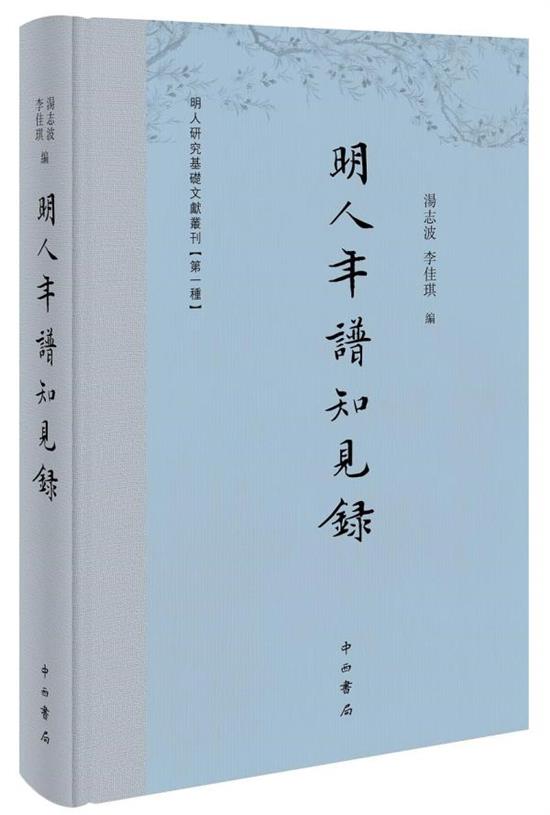
《明人年谱知见录》,汤志波、李佳琪编,中西书局2020年11月出版,400页,160元
较之拥有厚重的本土学术传统的魏晋南北朝史、唐史、宋史研究,或较之在全球视野下纵横发展的大元史、新清史研究,有关明代历史、文学、文献的研究,一直都不是学界热议的焦点。在历史研究领域,帝制中国晚期的社会化、地方化趋向,让社会结构理论与田野调查方法更有用武之地,围绕精英人物的年谱之学渐趋冷落;在文学研究领域,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,明清诗文研究倒开始“走出冷落”,成为古代文学研究中最活跃的学术增长点之一,但近世时代的文献特征及其文本的弱经典性,让很多学人迷失于荒野丛林之中。大家感慨明清文学研究有三苦,一苦于原始文献浩如烟海,二苦于别集文本无注可依,三苦于基础实证重复作业。如何解决这些问题,并没有终南捷径,我们只能依靠传统文史研究的三大法宝:叙录、笺注、年谱。明清虽同处近世,但清代人物研究的工具书相对完备,《清人别集总目》《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》《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》《清代人物生卒年表》《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》等,早已是学人案头的必备书籍;明代固然也有《增订晚明史籍考》《明别集版本志》《明人传记资料索引》《明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》等书,但在年谱目录与生卒年表这一块,梳理依然薄弱。有关生卒年的考证,现在通过计算机对海量文献的文本挖掘,或可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;但工作量更大的年谱编纂事业,在短期内尚难由人工智能来取代。反而,“新文科”视野下的历代人物数据库、古典文学知识图谱等工程,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前人年谱中的标准化数据。这个时候,对明人年谱的目录清理,尤显重要。
明人年谱到底有多少,这个家底一直不清楚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,我们只能通过杨殿珣《中国历代年谱总录》、谢巍《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》等书窥其一斑;对近三十年的最新编纂成果,更是缺少全面的普查。比起清人年谱目录早在三十多年前就有来新夏的《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》,且有持续的增订,同样在历史时间上延续了近三个世纪的明代,愿意问津者少。汤志波、李佳琪编的这部《明人年谱知见录》(以下简称《知见录》),著录明人年谱2106种,谱主1024人,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,相当于把来先生的“年谱知见录”事业向前推进了又一个“近三百年”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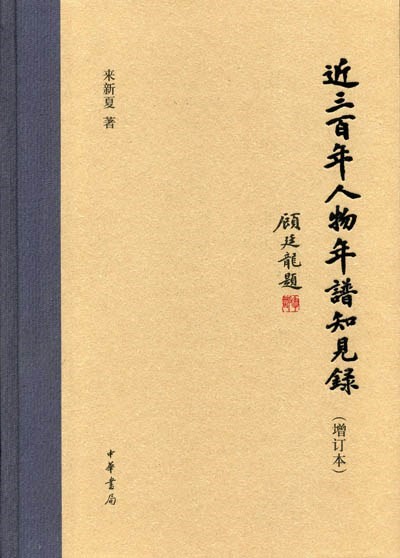
《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》
通观这部《知见录》,在感慨编者收罗丰富之余,我们亦须承认,在这些明人年谱中,真正被学界同仁普遍使用的并不多,类似傅璇琮《李德裕年谱》、孔凡礼《三苏年谱》、徐朔方《晚明曲家年谱》、章培恒《洪升年谱》那样,可以被学界列入“断代文学研究推荐书目百种”的共识性年谱,尚不多见。多数年谱专书之间并未形成有效的学术关联,我这里所说的关联,并非历史记录的互见,而是指一部年谱在编纂伊始及其过程中,始终有与其他同时代人物年谱进行对话的学术诉求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明代文史学界,距离提供一套有关明人行实的系统性文献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在这方面,我们应该怎么做,有两个很好的参照系。一个是唐代诗人年谱。唐人的年谱,早期多见于两宋时期刊印的唐人文集的卷末附录,其内容简要,与现代年谱专书之详实,不可共语。其篇幅体量渐大,与清代实证风气下“诗谱”观念的兴盛有关。自此,“别集编年”与“人物年谱”两种著述体例紧密合流,并保持了良性的互动,让两种人物行实的编聚模式,都有了较充分的发展。现在公认的唐代主要诗人的年谱,虽编纂有先后,但不可否认,皆有赖于近三百年来历代学者在唐人别集笺注上的杰出成绩。而当代学者编撰的《唐代诗人丛考》《唐代文学丛考》《唐才子传校笺》《唐五代文学编年史》等系列成果,更从多个维度全面地提升了唐人行实世界的分辨率。这种“名家年谱”“人物丛考”“专题编年史”的三合一编聚体系,为唐代文史学界提供了一套可靠的基础实证文献。现今学界对宋人行实的考掘与整理,基本上照搬了这套编聚体系,明清人物研究若要效仿,也没有问题。
另一个就是明代曲家年谱。在这部《知见录》中,八木泽元《明代剧作家研究》、徐朔方《晚明曲家年谱》、金宁芬《明代中叶北曲家年谱》三书,出现频次很高,相当亮眼,共收录明曲家年谱53家57种。与唐人别集早在清代就有多种高质量的注本不同,明别集的笺注事业举步维艰。由此,明人年谱的编者便需要对海量的原始文献进行耙梳与考辨,才能完成对曲家行实的编年。包括邓长风《明清戏曲家考略全编》、汪超宏《明清曲家考》等采用了“人物丛考”的行实编聚模式,同样建立在大量未整理文献的基础之上。其中不少曲家的别集,时至今日仍没有注本甚至基本的整理本问世。这是对旧有学术传统中的年谱生成模式的一种逆动,在某种程度上,可视为当代学人通过对明人年谱的具体编纂实践,为谱牒学作出的一个特别的贡献。明人年谱要想进一步展开,对类似经验的总结尤为重要。
总的来说,名曰“知见录”,肯定是一种回顾的姿态。但在回顾中,我们也应尝试去观察某些或然的趋势。如果能把握住明代文献的特质及整体学术的脉动,那么,传统的研究方法同样可以参与到学术的前沿问题中去。私以为,在标准动作之外,日后的明人年谱编纂及目录建设,或可在以下四个方面着重留意:
第一,大力推动群谱的编纂。徐朔方先生在《晚明曲家年谱》中,已表露出明确的“群谱”编纂之意识,云此法借鉴夏承焘的《唐宋词人年谱》与英人谦勃士(E.K.Chambers)的《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戏剧》(The Elizabethan Stage),可谓既“向前看”,发扬本土学术传统;又“往外观”,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。西方史学传统中向有群体传记学(Prosopography)的概念,近年来借助各类人物传记数据库的建设,焕发出新的学术生机。而明代存世文献的数量,可以提供足够的人物行实信息并确保其中的知识密度,以支撑起群体传记学理论的本土建设。近年来,学界涌现了一批相类的“群谱”成果,如曲家群落研究方面,有金宁芬的《明代中叶北曲家年谱》;地域作家群落研究方面,有孙秋克的《明代云南文学家年谱》,陈庆元的《晚明闽海文献梳理》等。这既是对明人考实成果的集腋成裘式的整编,也客观地反映了近世文学发展中的某些群体性特征,有其必然及合理的一面。如果说《唐宋词人年谱》中的词家,很多在事实上并没有群体性的交集,更多是反映了编者的文学立场,那么,明清的文学家群谱,无论谱主是戏曲家还是地域作家,主要在反映文学流派产生、发展、互动的历史现场。若能有效地利用并创新“群谱”之体例,明清人物研究也能结出反映自己时代体貌的学术果实。
第二,顺应年谱长编的“前倾”之势。名家年谱的长编,本来是近现代人物研究中的常见著述形式。近年来,随着史料检索的便捷化、文献研究的精细化,渐有“前倾”的趋向。越来越多的宋元明清人物,被纳入“年谱长编”的学术事业之中。前辈学人一贯强调的史料当有取舍的编纂态度,在学术体系的范型转变中,亦须经受新的考验。近年来较有影响的年谱长编,宋代有刘成国的《王安石年谱长编》、束景南的《朱熹年谱长编》等;明代有束景南的《王阳明年谱长编》、周颖的《王世贞年谱长编》、薛龙春的《王铎年谱长编》等。在接下来可以预期的较短时间内,还有沈周、胡应麟、曹学佺、徐、祁彪佳等明人的年谱长编将陆续问世。总的来说,明代重要人物年谱的长编化,将是一个趋势。尽管没有像晚清、民国人物那样,有日记、报刊等逐日记录的文献予以普遍支持,但明人别集的刊刻及保存情况,以及别集中文本文献的即时特性、编次原则等,让人物行实的“逐日编次”成为一种逼近之可能。特别是那些文集在百卷以上的著名作家,一旦其年谱长编的工作正式展开,必将对人物行实的研究精度提出更高的要求,这对明人集部作品的细读及诗文的经典化来说,不失为一个形成双赢的机会。
《王安石年谱长编》
第三,重视行实碎片的编聚模式。《知见录》中的很多年谱,其实仍是半成品。它们多为专书或学位论文的附篇,其初衷并不追求独立的学术价值,而是起到匹配正文、对读释义的作用。这不难理解,年谱在唐宋时代创撰伊始,常以单独成卷的形式附录于文人别集之后,也是类似的情况。但随着大量研究生学位论文在中国知网、万方等学术数据库中公布,它们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公开出版物。一概视而不见,既是巨大的资源浪费,也导致不必要的重复劳动。如何有效地整合,开展深入的人物行实群考,总结出一套适合明代文献特点的编聚模式,既是机遇,也是挑战。唐代诗人的行实材料,其实比明人更碎片化,其中经验多有可学之处。故唐有傅璇琮的《唐代诗人丛考》,明清有邓长风的《明清戏曲家考略全编》。傅先生另主编有《唐才人传校笺》《宋才子传笺证》,晚年还有意仿《宋才子传笺证》之例,主编《明清才子传笺证》。其实,明代有自己的“才子传”,那就是钱谦益的《列朝诗集小传》。在这方面,日本汲古书院于2019年出版的野村鲇子编《〈列朝诗集小传〉研究》,可谓导夫先路。而更全面的考察,在即将问世的张德建的《列朝诗集小传笺证》,此书或将在一定程度上,实现对现有的大量年谱半成品中的明人行实考证成果的打捞、汇集与新证,为读者提供一套值得信赖的明人“群传考实”之书。另外,采用专题编年史的模式,编聚相类作家、学者的行实信息,如马美信《唐宋派文学活动年表》、吴震《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》等,也是一种尝试,但这已不在人物年谱的讨论范围之内了。第四,坚持年谱目录的在线更新。在某种意义上,《知见录》不仅是一部工具书,编者细大不捐的编纂态度,不唯供人按图索骥而已,同样意在以目录学的方式,保存一段有关明人行实研究的学术史。纯就“使用”而言,书中很多早期的简表、简谱,在更完整的年谱专书问世之后,基本上失去了学术参考的意义。既然关系学术史,那就需要形成一套全面、动态的著录机制。较之传统的纸质出版物的修订周期(如《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》初版于1983年,增订版于2010年),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工具书,理应以更积极的态度来认识并使用互联网、数据库等新技术的力量,实现纸质书籍与电子检索的并行,甚至让年谱目录的修订工作处于长久的进行时态。相信网络文本的即时性、公开性与低成本,可以让《知见录》成为一部拥有持久生命力的“新著”。
有关硕、博学位论文中的明人年谱情况,我想再多说几句。过去三十余年,以明人年谱作为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或附录,已成为指导青年学人的重要的学术训练方法,如果作者不甚满意,自然可以不拿出来。但对更多的读者来说,一代又一代的学术新人做了大量的知识生产,其成果未能进入公共的学术领域,而后来人又对曾经发生过的学术工作知之甚少,以致重复作业,其实是严重的资源浪费。当然,学界中人向有精品意识,由权威学者聚沙成塔的《唐代诗人丛考》《唐才子传校笺》等,是公认的标杆性的人物实证成果,而那些尚需磨砺的学位论文,确实离精品还有很远的距离,难具学术上的公信力,亦属正常。但不管怎么说,在《知见录》中著录了521部(篇)见录于硕、博学位论文的明人年谱,此数量不可谓不大,如何清理并挖掘其中的价值,应引起学界的重视。这是明清文学研究的独有特点,毕竟在傅璇琮先生等几代学人的努力下,现在很少再有研究生在学位论文中附录自编的唐人年谱了,而这种现象在明清文史研究中仍日复一日,相当普遍。若能借《明人年谱知见录》出版之机,触发一些有益的思考及应对之策,也是好的。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,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
